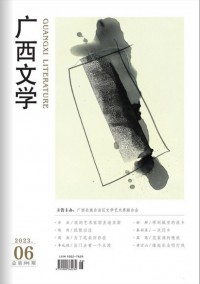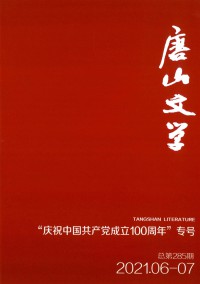文學創作論文范文精選
前言:在撰寫文學創作論文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學習和借鑒他人的優秀作品,小編整理了5篇優秀范文,希望能夠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借鑒。

文學創作中感情表露的分析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以意造象;思想情感;文學創作;外化技巧
論文摘要:以意造象是文學創作中思想情感表達的一種外化技巧,從古至今文學家們均普遍運用。以意造象應講求“意”的新穎、深刻;而“造象”應符合事物本質,要有象趣和個性,方能產生藝術魅力。
“以意造象”,是文學創作中思想情感的~種外化技巧,就是作者從創作意圖出發,調動自己的生活經驗,創造出適合于表達作者思想情感的形象。“意”即主觀的思想情感,“象”即客觀的人事景物。《周易·系辭上》:“圣人立象以盡意。”…‘造象”的目的,就是為了表達“意”。有什么樣的“意”,就會有什么樣的“象”。沒有“意”,就沒有“象”。人的思想情感是內在的、抽象的,而人事景物則是外在的、可感的。人的思想情感的表達,需要附載在具體的人事景物的形象上,即寓情于景,寓情于物等,才能被人理解、接受和引起共鳴,產生藝術魅力。
一、“以意造象”,在古典文學創作中十分常見。
如《詩經·關雎》中開頭四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描寫了水鳥歡快的應和嗚叫,表達了對美麗善良的姑娘的贊美之情。“關關,水鳥叫聲。王先謙《三家詩義集疏》:‘《魯》說日:關關,音和聲也。’……《玉篇》:‘關關,和鳴也。”《集傳》:‘雎鳩,水鳥。”,(詩中用起興手法,寫水鳥的嗚叫,是為了表達人的情感。或者說,是為了表達人的情感的“意”,才造了水鳥的嗚叫“象”。
又如杜牧的詩《長安秋望》:“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這是一曲對秋天的贊歌,贊美了遠望中的長安秋色。“秋”是詩人要表現的直接對象,詩人對秋的思想情感是要表現的間接對象。詩中寫詩人登高遠望,縱覽長安高秋景物的全貌,并用南山這個有名的歸隱之地來作襯托,使“秋”的形、神都得到了具體的描繪,更表達了詩人心曠神怡的感受和高遠澄凈的心境。“這首詩的好處,還在于它寫出長安高秋景色的同時寫出了詩人的精神性格。”“秋”之高遠無極的景色與詩人曠達胸懷的精神氣質躍然紙上,讓人心有所悟。
文學創作中荒誕哲學論文
一、加繆文學創作中的荒誕哲學
1.機械式的生活與麻木的精神狀態加繆在其文學作品中,對于荒誕的表現主要就是通過對人庸常生活的機械重復式描寫以及無意義的敘述,并表現了人的精神世界的麻木狀態。比如,加繆的小說《局外人》與《鼠疫》以及散文《人身牛頭怪》中就使用了大量的篇幅來描述人們的一成不變的僵化生活狀態。在《局外人》中,默爾索在枯燥乏味的辦公室里過著沉悶的日子,即使他的母親去世都無法改變他慣常的生活狀態。此外,他還描述了人們百無聊賴的精神生活。比如,《局外人》中的老頭與狗相互憎惡,但又相互形影不離,這是一種深入骨髓的精神折磨。還有些老年人迷戀自己精心修筑的墳墓,這是一種怪異的行為舉止,甚至成為了一些老年人維系生活、支撐精神的支柱。實際上,這是加繆通過對老年人無聊生活的描述來傳達自己對于人類生命趨向終結的自我認識,抒發了自己對于世界荒誕、人生有限以及生活虛無的深刻反思。在文學作品中,加繆對于年輕人生活狀態的描述則是為了傳達出人類對于荒誕世界的應對態度與反應,即認為人類通過種種自我麻痹的方式來回避荒誕的存在境遇,從而慢慢地習慣了機械僵化的生活模式,處于一種麻木不仁的精神狀態之中。
2.神秘難解而又無法逃避的異己力量加繆的文學作品中對于荒誕哲學的應用與滲透,還表現在對一些神秘莫測而又不可理喻的異己力量的描述。這種力量有時又是無法逃避和回避的。比如,在他的戲劇作品《誤會》中,他就敘述了一個死亡的悲劇故事,其中蘊含了某些具有一定支配性力量的神秘但又荒誕的力量。若望回家后卻被親人殺害,瑪爾塔與母親為了開始新生活不料毒死了親人等。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稀奇古怪的事情,卻似乎又讓人感覺無法抗拒和逃避。這是加繆對于荒誕哲學的巧妙運用,讓作品中出現了種種本意與現實、希望與實際之間的巨大反差,甚至讓事件向著完全相反的方向發展。這個作品的題目就很好地闡述了荒謬的巨大力量,它會操控人的命運發生非此即彼的結果,并且是不可逆轉的。
3.人與世界之間的疏離感加繆上面的兩種荒誕的解釋與表現手法,實際上都說明了一個問題,即人與世界之間的疏離感。比如,《局外人》中的默爾索過著的一種局外人的生活,他的生活狀況是封閉的,整個生活方式與生活處境都反映了他作為一個個體的人與客觀世界之間是斷裂疏離的,從而也充分揭示了人與社會、人與他人之間的疏遠隔離的生活狀態。在默爾索看來,整個生活就像是一個大機器,人們都過著一種如同齒輪般運轉的生活,表面上一切井然有序,實際上就是生活在一個牢籠里。因此,他就像一個局外人一樣,能夠發現生活中各種荒誕的景象,并有著局外人獨有的觀察方式與處理方式。比如說,他在面對母親死亡的時候,并沒有在葬禮上表現出常人的悲傷與哀痛,因為他認為每一個都難逃一死,母親的去世只是真理的表現而已。他認為整個世界是陌生且難以解釋的,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無足輕重的,任何遠大理想都是徒勞的,任何榮譽都是無價值的,人們都生活在一個虛無飄渺的世界中。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這說明了人與世界之間的巨大疏離感。
二、西西弗神話中的荒誕哲學
1.發現荒誕法國作家加謬在文學創作中滲透進荒誕哲學的理念,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把生活中的荒誕的一面很好地展示在讀者面前,引領人們更為清晰地看清楚客觀世界,對于現實世界中的荒誕現象有一個更為清醒的認識。事實上,人們要想發現生活中的荒誕并不是很難的,有時幾乎就是一種油然而生的狀態,在習慣了的生活方式之下,猛然之間做出的反應,即忽然發現了生活中的荒誕。當然,這種反應也許是對生活的厭倦,抑或是失望,也有可能是警醒。發現荒誕必須依靠人的意識,否則,麻木不仁的人是無法發現荒誕的。那么,在他的隨筆集《西西弗神話》中,加繆描述到人們的生活是遵循著既定的生活模式,但是,一旦有一天人的意識忽然被激發出來,就會提出為什么這樣生活的問題,這就意味著人們在機械式麻木生活模式的規制下,開始萌發了意識運動,其結果是無意識地重新套上先前的生活枷鎖,也有可能是徹底的覺醒,對枯燥生活發出通牒,表達出種種厭倦和不耐煩甚至于反抗。
東北文學論文:談論東北文學創作媒介與文學社團考
本文作者:葉立群單位:遼寧社會科學院
在進步愛國的文學副刊中,影響力最大的是《大同報》《夜哨》文藝周刊。這個周刊有兩大特點。第一,立場鮮明。編者陳華在1933年8月6日的刊詞《生命的力》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不要“彷徨,躊躇”,要起來“以自己為武器去抗爭”。文學史對此做出了中肯的評價,“從《夜哨》發表的大量作品來看,體現了編輯的宗旨。最鮮明的特點是:一些進步文學青年所描寫的對象,已由過去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我表現,開始轉向工農勞苦大眾。所反映的思想內容,除暴露社會的黑暗外,同時指出斗爭的方向,預示著前途的光明”[1]137。第二,以此為陣地的進步作家多,作品的社會反響大。在共出刊的21期《夜哨》上,發表了蕭紅的短篇小說《兩個青蛙》《啞老人》《夜風》等,蕭軍的短篇小說《下等人》,羅烽的短篇小說《口供》,金劍嘯的短篇小說《星期天》,李文光的短劇《黎明》和中篇小說《路》。這些作品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反響,激發了飽受凌辱的民眾不畏強暴、勇于反抗壓迫的信心。“九一八”事變后,盡管東北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對淪陷區文學活動的領導,甚至直接領導創辦文學副刊。其中《哈爾濱新報》的《新潮》副刊即為黨直接領導的重要副刊之一。“這個副刊是由一些進步文學青年創辦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公開的報紙文藝副刊。報館地址在哈爾濱道外十三道街。經常為副刊寫稿的有:羅烽、舒群等。”[2]14《新潮》發表的作品,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深刻揭露了日偽統治下的反動和黑暗社會本質。《新潮》共出刊半年,1932年9月,松花江大水沖垮了報館,副刊也隨之停刊。淪陷區存在時間最長的進步文藝副刊是白朗在《文藝協報》主編的《文藝》周刊。從1934年1月18日到12月17日,共出48期。作品主要有連載小說、詩歌、散文、連載文論,作者包括金劍嘯、羅烽、白朗、蕭軍、蕭紅、舒群、代生、梁山丁、唐景陽等地下文藝工作者與進步文學青年。代表作品有蕭軍、蕭紅合著的短篇小說《一個雨天》《鍍金的學說》《破落之街》《期待》《患難中》,蕭紅的小說《麥場》《麥場二》,金劍嘯的《云姑的母親》,梁山丁的《黃昏的莊上》《無從考據的消息》,白朗的《逃亡的日記》《四年間》等。這些作品真實地描繪了當時農村的破敗,人民的悲戚生活,也反映了人民的反抗情緒和抗爭精神。
壓制與抗爭———淪陷期文學期刊的“歌與哭”東北淪陷時期文學期刊的產生,其背景是復雜的,發生發展過程是曲折而艱辛的。最初允許創辦文藝期刊,在政策層面仍然是日偽統治者出于統治的需要,想借此擴大宣傳,美化日偽政權。但推動文學期刊走向繁盛的最重要的動力,卻是文學自身發展的需求。淪陷區最早的期刊是1932年創辦于沈陽的《大同文化》,后辦刊地點又經兩次遷移:1935年4月遷長春,1936年3月遷大連。“該期刊內容多系宣傳所謂‘滿洲建國’的意義與闡述‘王道主義’的文章,以及美化日偽政權的文藝作品。這是敵偽統治者的御用刊物。”[1]1401932年,《淑女之友》在沈陽創刊,該刊發表的文藝作品雖在文藝界產生較大影響,但多屬唯藝術而藝術的作品。隨著文學創作隊伍的成熟,報紙的副刊因其容量有限,已經難以適應豐富的文學內容。于是,那些革命的和帶有進步傾向的創作者開始開辟新的陣地,創辦大型期刊。1934年底,當時最具影響力的《鳳凰》在沈陽創刊;1935至1936年,《新青年》《興滿文化月報》《滿洲新文化月刊》《斯民》《滿洲文藝》等先后創刊。“期刊的出現,改變了文學創作完全依附于報紙副刊的局限,篇幅的增大,作品表現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也就有了比較充分的展現,東北文學的發展有了適宜的陣地。”[3]116《鳳凰》是帶有明顯進步傾向的期刊,刊登了大量介紹國內文藝動態和進步作家情況、作品及評價的文章,發表了如蕭然的《漢子》、吳瑛的《夜里的變動》、扉子的《老聶的話》、尹鳴的《小三子的命運》等在當時產生較強反響的進步作品。其他幾種期刊刊登進步作品,則要策略得多。如《新青年》是協和會奉天省事務局創辦的,在發刊詞中強調其辦刊宗旨是“統一青年思想”“克制外來之思想”“復興滿洲之文藝兵挽救出版局之沒落”。盡管如此,進步作家仍然沒有放棄這樣的陣地,他們仍然在壓制中發出吶喊。刊于《新青年》的馬尋作品《宵行》,秋螢作品《雪地的嫩芽》,都是通過較隱諱的方式,抒發了思鄉之情,揭露了敵人的殘暴。1937年后出現的較有影響力的期刊有《明明》《藝文志》《文選》《作風》《新滿洲》《麒麟》《青年文化》等。與上一階段相同,這一時期期刊的公開辦刊宗旨更多為日偽政權服務,如《藝文志》標榜兼收并蓄,鼓勵寫與印主義,實際上是鼓吹為偽滿洲國振興文藝。《新滿洲》提出“以忠愛孝義協和為宗旨”。這些期刊發表了許多為日偽統治涂脂抹粉的文章。《文選》是當時斗爭性最強、刊登進步作品最集中的期刊。時任《文選》編輯的進步作家秋螢在創刊號的《刊行緣起》中指出:“現階段的文學已經不是超時代的為藝術而藝術,或個人主義的牢騷泄憤了。現在的文學是教養群眾的利器,認識現實的工具。”《文選》共發行兩期,首期刊載的進步作品有山丁的《狹街》、白樺的《飲血者》、石軍的《擺脫》、姜靈非的《三人行》等。第二期刊載了李妹人的中篇小說《鍍金的像》、秋螢的中篇小說《礦坑》。這些作品,通過各種形式,反映出了被奴役、被壓迫的農民、市民和礦工的悲慘境遇和反抗的心聲。淪陷期文學期刊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它們成為文藝論爭的重要載體。1938年后,淪陷區文藝界爆發了激烈的文學論爭,出現了兩種對立的文學觀,一種是提倡“描寫真實”“暴露真實”的文選派觀點,一種是倡導“寫與印”主義的藝文志派觀點。1937年,日本人城島舟禮創辦的《明明》提出了“寫印主義”的倡導,在創刊紀念特大號發表了“百枚小說”(即400字原稿紙100頁),隨后又推出了“城島文庫”叢書,出版了古丁、小松、爵青、石軍等人的作品。《明明》停刊后,古丁、小松、爵青等人在《藝文志》的發刊辭上提出“藝文之事,端在寫與印,其所寫,無嫌天地之大,芝麻之小,倘有真意,自可求傳;其所寫印,無論滄海之巨,粟粒之細,倘存善根,當能久遠。”大力倡導“純藝術”。文選派觀點的明確提出始于山丁發表于《明明》的《鄉土文學與〈山丁花〉》,他指出:“不論在時間和空間上,文藝作品表現的意識和寫作的技巧,好像都應當側重現實”。
并且強調:“滿洲需要的是鄉土文學,鄉土文學是現實的。”山丁提出“鄉土文學”的主張后,馬上遭致藝文志派的批評,嘲諷“鄉土文學”作者亂提主義,指責“鄉土文學”是地域主義,有偏狹性。隨后,山丁、秋螢、梅娘、袁犀、金音、冷歌、李喬等,陸續在《文選》等期刊發表文章,批評寫印主義,極力倡導不能逃避客觀現實。沉默中的吶喊與屈膝———淪陷期文學社團的“功與罪”在東北淪陷的14年中,文學社團異常活躍,高峰時有據可查的社團就達二百多個。由于當時復雜的社會生態,社團的成因、訴求、形態也有著很大的差異。最早的文學社團出現在1933年初,它們萌芽于文學愛好者的聚集交流,后依托日漸興盛的文學副刊而成熟,到了1934年即在數量和影響力上達到了一個鼎盛期。1934年11月3日《滿洲報》載文提到的文學社團就有19個,即:冷霧社、新社、飄零社、白光社、白眼社、白云社、新潮社、紅葉社、旭日社、曦虹社、濃霧社、凋葉社、落潮社、野狗社、ABC社、寒光社、寒寂社、凄風社、春冰文學研究社等。其中最有成就的社團是冷霧社、新社、飄零社和白光社。這些社團的重要特點是屬于依托副刊自發形成的同人社團,各有鮮明的創作追求,團結和培養了大批作家。其中冷霧社依托沈陽《民報》的《冷霧》周刊,主要成員有成弦、馬尋等;飄零社依托《撫順民報》的《飄零》周刊,主要成員有孟素、秋螢、曼秋、石卒等;新社依托《沈陽民報》的《蘿絲》周刊,主要成員有楊蕭梅、碧波等;白光社依托自印社刊《白光》和《奉天周報》的《白光》周刊,主要成員有小松、雪萍、夢園、文文等。四大社創作特點鮮明,被研究者評價為:“標榜追求完美的冷霧社;因襲歐洲古典創作的新社;貼近現實的飄零社;講求純藝術的白光社。”[4]6東北淪陷后期,隨著報紙副刊的凋零和期刊的興起,出現了依托期刊的文學社團。這些社團的特點是規模較大、審美趣味和藝術主張更為明確的、創作園地更為堅實廣闊。其中明明派(藝文志派)依托《明明》和《藝文志》期刊;文選派依托《文選》期刊;文叢派依托《文叢》期刊。這些社團在創作的同時,堅持自己的文藝主張,并進行了長期的藝術觀念論爭。在日偽的白色恐怖統治下,淪陷區抗日愛國的文化人士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斗爭。在這一時期,產生了“L•S(魯迅)文學研究社”和“馬克思主義文學小組”等進步文學社團。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詩人田賁組織的“L•S(魯迅)文學研究社”。這個文學社1936年創辦于遼寧省蓋縣,主要參加者為田賁曾經的同學、學生和文友。他們秘密傳遞借閱進步報刊,研讀左翼書籍,利用文學創作揭露日寇侵略罪行并喚醒受壓迫的同胞。后又創辦了《行行》《星火》等刊物,宣傳抗日愛國思想。哈爾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小組”的領導人為共產黨員陳紫(關毓華),成員包括關沫南、宿學良、劉煥章、王忠生、佟世鐸等。他們積極組織進步青年,以文學創作進行抗日活動。在日偽統治者的嚴密控制下,文藝界的反抗斗爭雖如野火般旺盛,但終究還是要在地下奔涌。那些御用文藝組織和反動的日本作家同人文藝團體卻大張旗鼓的活動,蒙蔽民眾,毒害人民。主要的日人作家同人文藝團體包括“滿洲浪漫”“作文發行社”“鵲”“撫順文學研究會”“滿洲短歌會”“北滿歌人社”“大連川柳會”“滿洲新短歌協會”“關東洲詩人會”“滿洲誹句會”等。1941年3月23日,日偽政權出臺《藝文指導綱要》,規定文藝團體組織、研究機構,一律由敵偽政權直接領導。
隨之,日偽扶植的御用文藝組織“滿洲文話會”“滿洲藝文家協會”“滿日文化協會”“藝文志事務會”等紛紛成立。日偽政權為這些文藝組織提供資金,支持他們的活動和出版。他們創作了大量的漢奸文學和殖民文學,粉飾美化王道樂土,歌頌侵略戰爭,攻擊中國人民的反抗斗爭。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作用。
西方文學創作的的歷史發展過程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貴族化;平民化;自然主義
論文摘要:西方文學從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貴族氣息,中世紀起逐漸有了平民化意識。文藝復興時期這種意識有了一定發展,啟蒙文學時代有了更大的發展,直至自然主義文學興起,最終完成了向平民化的轉變。文學作品從以表現貴族人物為主轉向了以表現普通、平民人物為主;從以表現帝王將相、英雄人物的活動為主轉向以表現普通、平民人物的活動為主。
西方文學從一開始就存在貴族化傾向。這表現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上。歐洲文學的源頭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學,而史詩和悲劇是古希臘、古羅馬的代表作品,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帝王將相或者是勇敢無比的英雄人物。史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荷馬史詩》,它由《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分組成。《伊利亞特》以“阿基琉斯的憤怒為主題”,圍繞著特洛伊和希臘之間的戰爭,主要描寫了英雄阿基琉斯、赫克托耳以及聯軍的首領阿伽門農這些貴族人物,在《奧德賽》中同樣也是圍繞著貴族人物奧德修斯來寫的。古希臘產生了對后世有巨大影響的三大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彼得斯,他們的代表性作品《俄瑞斯特亞》《埃阿斯》《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阿爾刻提斯》《希波呂托斯》《瘋狂的赫拉克勒斯》等,所描寫、突出、刻畫的都是貴族化的人物及其活動。
古希臘、羅馬的文藝理論中貴族化的傾向也比較明顯,如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中關于悲劇的主角的論述:“憐憫是由一個人遭受不應遭受的厄運引起的,恐懼是由這個這樣遭受厄運的人與我們相似引起的……此外還有介于這兩種人之間的人,這樣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運,不是由于他為非作惡,而是由于他犯了錯誤,這種人名聲顯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特斯以及出身于他們這樣家族的著名人物。”“出身于他們這樣家族的人物”主要是指貴族階層的人物。
一、中世紀西方文學平民化意識的開端
10至11世紀的歐洲各國出現了以手工業和商業為中心的城市,那時的封建社會進入了全盛時期。城市的發展產生了城市文化,出現了非教的學校和反教會的“異端”運動。于是,教會在思想文化上的壟斷被打破,非教會的世俗文化形成,城市文學也應運而生。城市文學是在民問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作者大多是城市街頭說唱的人,“作品也大多取材于現實生活,表現市民階級的機智和狡猾,諷刺專橫的貴族、貪婪的教士和兇暴的騎士”。法國是當時城市文學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有很多作品表現市民們的機智、靈活和重實際的特點。農民也是笑談中經常出現的人物。他們的機智和講究實際的特點使自身得以擺脫困境,獲得令人稱好的結局,如《神父的母牛》《農民醫生》等。城市文學的作者大多是沒有受過文化教育的普通人,不知道希臘史詩和悲劇,也不知道理論家亞里斯多德和賀拉斯,所以他們在寫作時不受古典傳統中陳腐規則的束縛,在作品中能自由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法國鬧劇《巴特蘭律師》中描寫巴特蘭律師與羊倌捉弄布商,最后巴特蘭被羊倌捉弄。該鬧劇揭露了商人的貪婪和法律的腐敗,也反映了勞動人民的困苦處境,表現了作者的市民階級意識。但像這樣的作品在當時為數不多,因為教會文學仍然占據著統治地位,封建社會中特有的騎士文學等還都是貴族化的文學,所以從中世紀開始才產生了平民化文學的意識。
世說新語的文學觀念及活動探討
論文摘要:《世說新語·文學》一門,以言說軼事這種獨特精省的方式,展現了中古時期在文學觀念、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方面斐然的成就。首先《文學》篇中呈現出兩個時序系統,即“學”系統和“文”系統。這兩個系統有顯著差異,表現出新的“文學”觀念。其次《文學》篇在文學創作中表現出反對蕪雜不裁,重獨創、反對事事模擬,重聲律等思想。這些文學現在文學品評方面對后世產生了較大影響。
論文關鍵詞:世說新語;文學;文學創作;文學批評
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是一部寫魏晉士人生活的百科全書,所記之事,自后漢迄于東晉,共分三十六門,保存了大量魏晉時期的歷史文獻資料,反映魏晉士人的思想狀況。其中,《世說新語·文學》一門,以言說軼事這種獨特精省的方式,為我們展現了中古時期在文學觀念、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方面的斐然成就。
一、《世說新語·文學》的“文學”觀念
《世說新語·文學》篇共計104條,第1至65條涉及經學、玄學、佛學等內容,主要記錄了關于注解經文的軼事;第66條以下至最后104條,則主要記錄了創作詩文的軼事,涉及到更多的是文學創作、文學評論等具體的文學活動,與今日所謂的“文學”觀念相接近。這兩個部分之間的排列在《世說新語》中是非常特殊的。《世說新語》的其它各篇,大都是按照時代的先后編纂相關材料。而《文學》篇從第66條,曹植“七步中作詩”則重新回到曹魏時代,以下始自成時序,于是在《文學》篇中就呈現出兩個時序系統就內容而言,按照今天的分類觀念,大體可分為“學”系統和“文”系統。
1、“文”與“學”的相通